来自美国波士顿

微信扫码关注公众号进行登录


完善安全信息
为了您的账号安全,请完善以下信息


来自美国波士顿
更专业的论文润色机构
微信扫码登录
微信扫码关注公众号进行登录


来自美国波士顿
更专业的论文润色机构
手机验证码登录
账号密码登录
微信扫码登录
微信扫码关注公众号进行登录
艾德思:许知远理想的书房是一整个图书馆

从早年的媒体人,到参与创办单向空间,再到近年因录制视频节目<十三邀>爆红,许知远一直以网红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.直到历时五年撰著的新书<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1873-1898>出版,他作为严肃写作者的一面才得以再度展露.
单向空间·东风店位于北京朝阳区驼房营南里的东风艺术区内,楼下是书店,楼上是许知远的办公室.这里是许知远日常工作/阅读和写作的地方.最近五年,因为埋首写作梁启超传记,书架上累累叠叠都是近现代历史类书目.梁启超像一个辐射点,其能量和光芒涉及传统知识/西学/教育/政治/新闻媒体/科技与思想变革诸多领域,牵扯出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.为了全景式再现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及其同代人,许知远搜罗了几乎所有相关书籍,这意味着一本400页左右的传记背后惊人的阅读积累.
作家的书房与他的作品息息相关,那里隐藏着写作不为人知的秘辛与甘苦.许知远的写作是半学术型的,因此他的读书极有目的性,为了治学/释疑或钩沉史实.他的阅读则是流动的,新的阅读兴趣靠空间的变换激起.他喜欢阅读传记,青年时代从北大图书馆偷走一本<李普曼传>,视若珍宝,为此还交了23元的罚款.
面对"私家书房'的采访,许知远坦言,许多书好像买来不是为了读,而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焦灼.作为书店创办者之一,他对私人拥有的书房无甚兴趣,理想的书房就是一整个图书馆,有浩瀚无垠的藏书."在书架间晃荡,总会有意外的发现',对他个人而言,"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在不同地方的图书馆发生.'
{访谈}
想去看看卡萨诺瓦的书房
南都:请介绍您的书房.这间书房有多大面积/大概多少册藏书?
许知远:我对书房没什么概念.我喜欢图书馆,比较浩瀚.也喜欢书店.这个办公室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,有我比较常用的一部分藏书.这部分藏书基本上和近现代历史有关系,因为我正在写梁启超传记的第二卷.您看这里有<章太炎全集><李鸿章全集>……各种各样的这些资料比较多.隔壁是我同事的办公室,也是放我的书.
南都:您通常购买哪些方面的书籍?
许知远:我买的书跟我研究相关的比较多.其他的,看它封面设计好不好看吧.买了书根本读不了,没有时间读.好像买来不是为了读的,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焦灼的.因为我买了,通过占有来遗忘自己没有时间阅读这个事实.
我没有特别规律性地去藏书,某种意义上它充满了很强的实用性和目的性.当我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,书房里就堆满了类似的书.现在这里的书很大程度都跟近现代中国历史/亚洲历史有关系,因为我在写青年梁启超的书,所以大部分是比较贴近他的.比如现在我读的这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的<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>,跟我现正在写的梁启超第二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.
我现在读闲书的时间越来越少.这让我感觉非常沮丧.闲下来乱读的就算闲书.有些作家我会买比较多,有些作家我会尽量收集,比如奈保尔/旅行作家简·莫里斯.更现实一点,目前市面上所有关于梁启超的书我都会找来.
南都:您觉得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的?
许知远:就是整个图书馆,好多藏书.我自己不可能实现.所以公共图书馆很好啊,它就是一个理想书房.如果未来中国能够有一个好的公共图书馆,那将是非常美好的.
我以前喜欢去国图,那儿安静,唯一的缺点是不能躺,只能坐着看.但是在书架间晃荡,总会有意外的发现.我以前也经常去港大图书馆查资料.中国的好图书馆太少了,不够开放,比较麻烦.我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是在不同地方的图书馆发生的.我在北大图书馆偷了一本书,<李普曼传>.新华出版社,价钱2 .31元,我赔了十倍,23元.当时买不到那本书.那本书是我无意中在书架上翻到的.李普曼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专栏作家,写各种国际事务的分析,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美好的,对这个世界胡说八道,见不同的人,以评论世界为业.那是打动了我的一本书.后来我的朋友吴晓波策划再版了那本书,我给它写了个序.
我去伯克利大学,被震惊了.我问图书馆管理员可以借多少本书,他说可以借200本.剑桥大学只能借5本书.所以您觉得美国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,薯条也大,汉堡也大,车也大,借的书也可以很多.一种充沛的感觉.
大学时代很多时间我也不喜欢去图书馆.图书馆太安静了,也不能吃东西,也不能乱走.当教学越来越严厉的时候,越来越多人到图书馆也不看书,就是做作业去了,气氛变成了一个自习室,不像一个图书馆.图书馆应该是一个更freestyle(样式自由)的地方.
所以我开始去书店.那时候北大南门有风入松/国林风/万圣,尤其夏天那里面开着空调,穿着拖鞋在里面泡一下午,翻各种乱七八糟的书,度过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光.
我对私人占有一个书房毫无热情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我对藏书,对这本书是不是属于我也毫无热情.我只要能读就好了.
南都:您的写作也是在书房里进行吗?
许知远:我很多写作是在咖啡馆里,在酒店酒吧的吧台上,在大排档上.我喜欢在跟书无关的地方看书.我最高效阅读的时候是在飞机上,在火车上,在酒店里临睡前.我是一个移动中的阅读者,我不能困在一个地方.我特别喜欢空间变化.我需要到一个地方才能读书.我最近几年老去日本旅行,我是不断地旅行/见了很多人之后,才重新勾起阅读的欲望.或者是到了现场之后才会想去读.
我以前很喜欢日本的一个很怪的政治人物,他是19世纪末<明治宪法>重要的起草人之一.比如说他去维也纳,到了维也纳以后他哪也不去,躲在旅馆里读所有关于维也纳的书,关于欧洲历史的书.读完之后再换一站,再去读.他也不出去看.我特别理解他.我觉得这种阅读者很有意思.但那个现场会给人很多很奇怪的感觉.
南都:最近出版的新著<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1873- 1898>这本书在哪里写就的?
许知远:在旧金山写了一部分,在横滨写了一点,在北京写了比较多.大部分是在北京写的.在旅途中也会写.在飞机上也会写.在长沙/武汉好像都写过.
南都:如果可以去到一位作家/艺术家/学者(已故或健在)的书房里去做客,您最希望探访谁的书房?
许知远:我想去看看卡萨诺瓦的书房.卡萨诺瓦是当年欧洲特别有名的一个浪荡子.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出一本回忆录,因为他一生有那么多经历.但他同时是一个很博学的人.我很好奇,他晚年安静下来的时候,他被什么样的书包围着.
南都:如果可以邀请一位作家/艺术家/学者(已故的或健在的)到您的书房来做客,您最希望邀请哪一位?
许知远:娜塔莉·波特曼,<黑天鹅>的女主角,她还演了奥兹小说改编的电影<爱与黑暗的故事>.我对她挺好奇的.我觉得她应该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女孩子.可以聊聊天吧,各种瞎聊呗.
梁启超是一个书单爱好者
南都:<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1873-1898>写了五年,在这五年里,您做了哪些田野工作?我听说您走访了广州/上海/北京/天津等城市,这些走访带来了怎样的收获?
许知远:很多资料可以从文献中得来.收获的是感受.我进到广州的餐厅里面,吃早茶时广东话那种人声鼎沸,点一个菜端上一盆蛇肉,食物的那种异样……您就会更理解梁启超生活在怎样一种语境之中.这种东西有助于对气氛的理解.
南都:您希望读者看到一个怎样的青年梁启超?
许知远:那是他们的事情了.我只是尽量写出这样一个人.有的人可能喜欢他的友情,他和朋友的关系.有的人可能喜欢他那种壮烈的东西,他和谭嗣同的分手.有的人可能喜欢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的热诚.有的人喜欢他的谦逊.都可能.所以我没有说要传递给读者,某个东西是您要知道的.文本有它自身的逻辑和价值,那是您自己寻找的结果.
南都:是否研究过青年梁启超阅读的书籍和他的阅读习惯?
许知远:我知道他喜欢晚睡晚起.他不是个爱起早的人.他是那种非常杂乱无章的阅读者,可以同时应对很多信息.他是一个高速的信息和知识的处理器,处理能力非常强.
在时务报馆期间,他的办公室和住的地方是混在一起的.上海的四马路是现今的福州路,衰落的书店街,书都按斤卖,当年却代表一种新思想.时务报馆在四马路上.那是一个很紧张的小屋.他的太太/他的弟弟都住在这儿.厂店合一一样的.四马路是旧上海很繁华/很有趣的一个地方.它一半是报馆/出版社/书店,另一半是茶馆/西餐厅/青楼,非常混杂的一种情况.高度感官和高度智性的生活同时很活跃.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,是一个对新世界的窗口.各色人等在穿梭,从山东/四川来上海买东西的人,他们要在里面交际,这里是一个交际场.很多新思想/社团又在这种交际中诞生.它是维新志士们的舞台,也是各种虚荣,各种奢侈/喧闹的舞台,其中良莠不辨.
梁启超当时也有给学生开过书目,西学要读什么书,中文要读什么书,书单不就是他读的东西吗?他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个爱开书单的人.这背后是一个知识分类的问题.新知识涌来,旧知识沉淀,怎么去应对这么一个混乱的知识世界?开书单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的路线图,是对知识的重新梳理.他要成为自己意义上的w ikipedia,目录学式的检索/分类,我相信他要创造自己的维基百科,自己的谷歌.
1873年,梁启超20岁的时候,他的第一本著作叫做<读书分月课程>."四库之书,浩如烟海,从何处读起耶?'他把学问分为五类:经学/史学/子学/理学/西学,给出了一个六个月的速成书单.他要求学生先读<万国史记>,其次读<瀛寰志略><列国岁计政要><西国近事汇编>,此外还有天文学著作<谈天>,地质学著作<地学浅识>,基本上在今天就像下载了一个得到APP一样.
更多科研论文服务,动动手指,请戳 论文润色、投稿期刊推荐、论文翻译润色、论文指导及修改、论文预审!
语言不过关被拒?美国EditSprings--专业英语论文润色翻译修改服务专家帮您!


特别声明: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,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;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,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“来源”,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;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,请与我们接洽。
凡注明来源为“EditSprings”的论文,如需转载,请注明来源EditSprings并附上论文链接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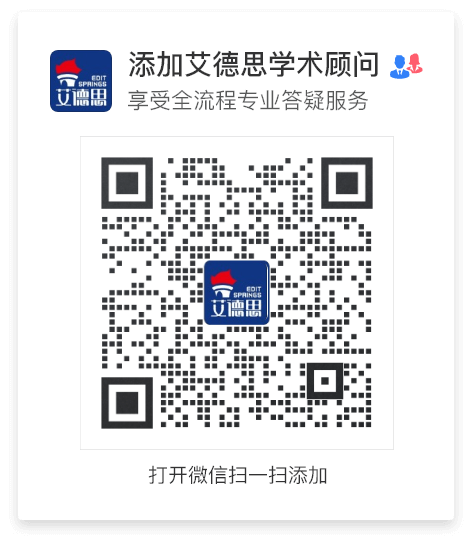


 鄂公网安备:
鄂公网安备: